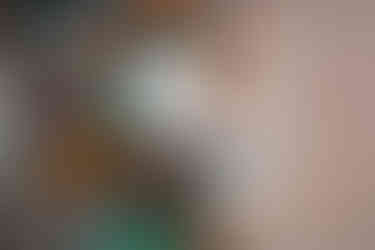坎坷揮就大景 生旦背後的畫師人生
- 屏風小編

- 2025年11月3日
- 讀畢需時 4 分鐘

潮州布景畫師陳冠良63歲了,他形容自己前半生「茫茫渺渺、坎坎坷坷」;學畫多年找不到出路,轉行想開烤肉店,又因臉皮薄怕被熟人撞見,離鄉背井跑到高雄大林蒲才敢開。這樣怕人窺見的人生,後來卻因明華園戲劇總團被更多人看見。他幫劇團彩繪的布景,不分軟硬,隨劇團演出跑遍全臺、離島,只要看過明華園的戲,肯定看過他的景。無論山林外景或宮廷內殿,可寫實逼真亦可金碧輝煌,景景層次分明。雖然僅是片薄幕,卻把舞臺上的虛幻,襯托的栩栩如生。
陳家是開布袋戲團的,到冠良師傅已是第三代。他小時候,戲團生意不差。他記得很清楚,「國小三四年級前沒序大人的概念,睜開眼看不到爸媽,他們都在外面忙,只有阿公阿嬤」。不過他爸不太想子女接班,因為早年內臺戲環境複雜,出入者不是走路就七淘人。他口才也不好,在唱作都得靠現場口白的年代撐不起場面,只能另謀出路。
老爸代筆交作業
勾出熱情但茫茫然
「認真想起來,應該是國小三年級啟萌。」陳冠良說,那次美術課作業由他爸代筆。雖是半世紀前的事,但他印象深刻,爸爸在畫紙上畫了一段廟宇的燕尾式正脊。那正是布袋戲的標準布景,他不記得老師給幾分,「只記得站在阿爸身邊,看他把畫畫出來的那種心情,好像有種東西被勾出來」。
這微不足道的生命插曲,開啟他的繪畫人生。賽洛瑪颱風重創臺灣那年,他國中一畢業即拜師學藝。一開始學廟宇彩繪及布景,但學8、9個月即換師父,再找擅長油畫、肖像的老師學藝,當兵前又改投另一位專畫電影看板師父。

「這段過程坎坎坷坷。」陳冠良說,他雖然口才不好,但家裡戲多時仍得幫忙,「金光戲盛行時,不會唸口白抓尪仔也可以幫忙摃炮仔,多個人也算多分力」。他學畫想求一技之長,但覺得前途渺茫,因此每個師父都跟不久,看到師父家環境差,當學徒反而增加人家負擔就放棄了。想說畫看板,看電影免錢又換師學藝。不管怎麼換,他心裡想畫的火苗從未熄滅,退伍後成家竟然還天天從潮州騎車去車城學畫。
(台語––◎序大人sī-tuā-lg:父母親。 七淘tshit-th礤:遊玩。 ◎走路ts-lōo:跑路、逃亡。)
輾轉學藝像發神經 36歲才遇伯樂
「那段時間很神經病。」他自嘲,每天一早去市場買菜,準備去老師家。那位師父從臺北返鄉照顧父母,擅長水墨山水花鳥人物,人稱「故宮派」。他心想總不能去老師家白吃白喝,每天備菜,像《論語》所指自行束攸到老師家。到了後稍事幫忙家務,清洗茶海等什麼都做,午餐後再拿畫給老師看。師父會指點其筆觸濃淡,前後差不多一年畫10張圖才結束。
被嘲發神經的經歷,卻讓他在以油畫、肖像為基礎的電影看板、布景技能外,又多了項水墨國畫技巧。但學這麼多仍不順遂,有段時間他幫樂宮、仙宮及富山戲院畫看板,但錄影帶興起,電影院打烊又一併把他的門關了。因為愛畫,後來索性開畫廊做裱褙,沒做起來又擺路邊攤賣圖,牡丹富貴、八駿馬都賣,但不是做生意的料,常一整天沒收入。後來又去市場賣衣服、賣自助餐,偶爾接案幫人畫廟宇布景,最後跑去高雄大林蒲賣烤肉,「只因那是沒人認識的所在,比較不會不好意思」。
如此摸索到36歲,才終於出現轉機。「有次遇到明華園藝術總監,」陳冠良說,「因為都是潮州人,陳勝福藝術總監惜才。」聽到他能畫託他畫布景,剛開始可能有點照顧同鄉半捧場的味道。但他把大半生學到的技法融會貫通,讓布景看起來有光影有層次亦有細節,總算迎來伯樂。
光影層次堆疊 老畫師猶有夢
「老實說,臺灣的布景、看板,從早年我學到現在都沒變化。」他解釋,因為這些都只是正式演出的陪襯,觀眾遠遠看,看得出形體也過關了。也因此不管布景或看板都是色塊堆疊,再加些簡單線條勾勒。但他覺得不夠,從打底色開始就想像光影變化,即便只是線條勾勒也有濃淡粗細,透過層次堆疊展現立體感。
這都是他坎坷學藝過程累積的心得。其中,布景分硬景、軟景,硬景得先釘木架作框、繃上畫布,之後再打線稿、上色,接下來細修拉線條,最後再上螢光漆才算完成。至於軟景,他正進行的一幅,寬36高14台尺(一台尺約30.3公分),整幅攤開只比標準羽球場小一點。如此規格,多數畫師會把整景攤在地上噴畫,他則吊起畫布手繪。因工作室高度限制,一次又僅能先畫10台尺,多餘的畫布只能先捲起來或捋在地上。
陳冠良一下盤腿坐畫綠草群山,一下又站到木桌上畫藍天白雲。以往一畫就到凌晨2、3點,手腳關節因長期摩擦長出厚繭,全身上下沾染油漬。但最可怕的不是這些,而是那些被捲起或捋著看不到的部分,整片景以拼接手法繪成,畫藍天時看不到湖水,難道成品不扭曲變形?他保證不會,因為所有畫面都在腦海了。
正因如此,明華園一次次把彩繪布景交給他,檔期已排到後年。他畫的山林外景,讓生旦淨末丑亮相演繹悲歡人生,王侯將相也在其手繪的金鑾寶殿中頭角崢嶸。他為傳統戲臺畫出不一樣的風景,但回望過去仍覺得所學不夠,「像水墨山水花鳥人物,那時很天兵,想說山水花鳥沒錢賺,直接學人物好了,至少可以畫神像」。陳冠良說,人生未必順遂,但他仍想畫且愛畫,若有機會仍想再學精一些,留下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。
出處:屏東本事2025秋季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