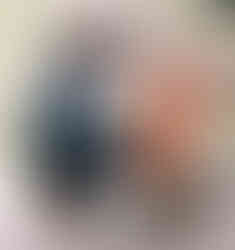給檳榔子開染房──iStudio COLOR
- 屏風小編

- 2023年11月8日
- 讀畢需時 3 分鐘

檳榔產業曾在台灣滋養好幾代人,早年傳唱一時的雙川調:「高高的樹上結檳榔,誰先爬上誰先嘗……」哼的就是那風光。
但高高樹梢後來被扣上枷鎖,山林水土保持、口腔癌……一道道枷項讓風光黯然。王一帆與黃琬婕夫婦兩年前移居內埔,發現它的新生命;他們以檳榔子染布,從粉藕色、奶茶色到咖啡色,百餘種檳榔子染獨有的紅棕色系布料,縫製成包,設計、用色至簡,風格卻不簡單,成就檳榔園裡新風光。
王一帆與黃琬婕兩年前因客委會客庄地方創生移居計畫,移居內埔客庄。兩人大學時期因交換生國際活動相識,之後愛情長跑多年成家,幾乎就要在台北城生根。因為琬婕的阿公阿婆(客語祖父祖母)住內埔,腦海裡有太多客庄生活印記,才啟動移居計畫。
「這行動要說是婦唱夫隨也可以!」王一帆笑說,他從小在台北長大,從決定移居到投入檳榔子染,都跟另一半有關。原來黃琬婕踏出校門後,曾有很長一段時間身兼數職。當年時下流行用語「斜槓」還沒出現,飄散濃郁文青風的市集也還未成形;她白天上班,下班回家就踩起縫紉機縫包,她對選布、縫包有個人特殊品味,在師大夜市賣出名號。
窮究檳榔子
開出檳榔園新風光
為了縫出夜市裡的獨一無二,甚至還專程出國選布,經營副業比正職更投入。他們現在產製的檳榔子染手提包,還沿用當時的「iStudio COLOR」品牌。這過程看來確是婦唱夫隨,但要把檳榔子染鑽到究竟,就非王一帆不可了。
王一帆說,檳榔子染在植物染盛行時期就有人做過,但多在紮染手法、染布質料上變化,若有接觸過檳榔子染,多半也屬體驗、手作性質。他查找資料發現,檳榔子染在七八百年前的日本鐮倉時代即已出現。以檳榔子萃取的染液,可染出特有的「檳榔子黑」,其特色是黑中偏紅,被日本人稱為「紅下黑」。另有種「藍下黑」,先以藍染打底,再覆以檳榔子染色。不論是紅下黑或藍下黑,都被視為家紋染色的最高等級。
為了成就日式檳榔子染的單一純粹,王一帆決定從檳榔子染定色著手。這看似簡單,但拆解開來卻是繁瑣功夫。首先得敲開成熟檳榔取出檳榔子,四百公克才得三分之一,之後下鍋萃取染液,得掌握水質、溫度,並調整硫酸銅等各式媒染劑配比,所有變量、變項都操控到穩固一致,色澤才告定著。
王一帆攤開試驗兩年多的成果,百餘張色票密密麻麻記載媒染劑配比。黃琬婕看著試驗成果笑說:「這工作只有台大圖資學系的做得來!」言下看似戲笑但其實頗有敬意,因為王一帆把課堂中習得的資訊比對、檢索功夫全用在定色上了,他手中的色票像電腦檢索還沒問世前的索引卡,規格標準且工整。依此操作,才可以染出塊塊色調精準的檳榔子染布。
打板縫包親為
回歸簡單生活
那天到黃琬婕內埔上樹村老家看他們染布,鐵皮屋裡阿婆正剪收檳榔,讓她看了想起舊時光笑說:「哈!我小時也做過喔,剪一大簍好像一百塊。」阿婆說:「現在更不值了,一粒才八分……」附和聲中王一帆已起鍋滾水準備染布,鍋中水汽蒸騰時,開始翻攪染布,空氣中剎時飄散奶香及青草香,彷彿大廚掌鍋的特有鑊氣,正是檳榔子染特有的氣味。
染布起鍋晾乾後,換黃琬婕接手。從夜市擺攤到現在,她仍是自己打板縫包。她設計的包款外型簡單,從肩背包到旅行袋,都沒夾層無內袋,攤開來看是不同色塊的組合,但隨著背帶調整及長短,同個包卻可變化出水桶包、托特包等不同包款。
「我自己是二寶媽,當然猜得到使用者想什麼。」黃琬婕笑說,有人問過她包裡為何沒夾層無內袋,其實那背後是她的生活態度。有人堅信得背上所有家當才有安全感,有人堅持得有包中包。但仔細觀察會發現,此刻需要的東西其實不多,回歸到簡單,心裡有安全感,簡單真不簡單!
去年他們以檳榔子染及創作參加GOOD DESIGN AWARD(日本優良設計獎),通過初審,今年參加屏東縣政府號召的屏東隊參加2023東京國際禮品展,也吸引多國買家目光。王一帆說,江戶時代檳榔子染因受貴族垂青,一度引發檳榔子搶購風潮。他們投入檳榔子染不單為了定色縫包,若有機會稍改農村風貌,甚至摘除一些檳榔的污名,一定會讓此趟移居更具意義。
出處:2023屏東本事秋季號